来源:一点儿乌干菜(ID:NarratorZhang)
作者:章程
一
村上春树的书我一直都没能读进去,大概那种温吞吞的笔调不适合我的秉性。不同于村上君,莫言的故事一出手就吸引我了,如同酒徒一头扎进了酒坛子。
从高中同学送了我《檀香刑》开始,莫言的小说就有一种独特的魔力召唤着我。我喜欢拉美文学大爆炸时期的那批作家。1957年春季,在巴黎街道上游荡的马尔克斯,偶遇海明威,狂喜着摆手对海明威喊出“大师”。几十年后,马尔克斯、富恩斯特、科塔萨尔相继离世,他们的拥趸们却再无这种福分了。
马尔克斯遗憾自己从未见过福克纳,只能靠布列松拍的那张著名肖像,想象“在两只白狗旁边,穿着衬衫在手臂上抓痒的农夫模样”的他。莫言也流露出过想见到福克纳的痴望:
“我熟悉他身上那股混合着马粪和烟草的气味,我熟悉他那醉汉般的摇摇晃晃的步伐。如果发现了他,我就会在他的背后大喊一声‘福克纳大叔,我来了’。”

布列松镜头下的福克纳
可是,福克纳也离世了。但福克纳与拉美的那些作家,我总觉得他们是不死的。在莫言身上我看到他们影影绰绰的身影,就像马尔克斯回忆他的外祖母给他说故事的时候,所有的祖辈们的鬼魅都在这间空荡的宅子里隐现,喃喃私语。
莫言在写作上的师承让我诧异又欣喜,总算寻到了家谱——这絮絮叨叨的意识流,魔幻又现实的一家子。毫无疑问,莫言是这个庞大的家族里的一员,并且是最接近我生命经验的一位。
这个家族,以马尔克斯等作家为首,诞生了多少富于想象力的创作。这个谱系满足了我爱听故事的喜好。当莫言力压村上君,荣膺诺贝尔文学奖而备受争议时,我倒是有种意料之中的窃喜,这帮老爷子们在中国土壤里成长起来的嫡孙,也是个不含糊的后生。
“莫言”这名字有意思。钱钟书的字叫“默存”,是因他小时候爱胡说乱道,父亲为他改的字,让他少说话。“莫言”当然是笔名,但寓意和钱先生的字一样。
莫言的成长期在八十年代之前,那个时代让“一部分人,因为各种荒唐的原因,受到另一部分人的压迫和管制”。莫言因祖先曾经富裕过,只读到五年级就被赶出学校。“在漫长的岁月里,一直小心翼翼,谨慎言行,生怕一语不慎,给父母带来灾难”。这“莫言”二字,其实是带着巨大恐惧的谨小慎微。
想噤口不言,却择了文字之志,且大半生以“说”为业,这也是无形中南辕北辙的有趣宿命。
二
我喜欢莫言早期的小说,《红高粱家族》《天堂蒜薹之歌》等长篇,以及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《白狗秋千架》等中短篇。
在看莫言小说的时候,我会不自觉猜测是一个怎么样的天才写出这恣意汪洋的文字,我猜想他小时候会不会是《丰乳肥臀》里的司马粮那样——“裤兜里装着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,有能在月光下变幻颜色的石头子儿,有可以切开瓦块的小锯条,有各式各样的杏核,还有一对麻雀的脚爪,两个青蛙的头盖骨。还有几颗牙齿,有他自己脱落的,有八姐脱落的,有我脱落的”。小时候的司马梁绝对是一个妙人,有韧性,死心眼儿。
司马粮对小舅上官金童说:“如果你存心要找一件东西,它自己就会跳出来的。”这话要不是带着一股痴气的憨劲,是决然说不出的。

姜文、莫言和巩俐
莫言身上就带着这样一股子憨劲。他老实巴交的模样,算不上好看,但土头土脑,憨厚朴实。毋宁说:莫言,憨人一个。
这种憨,学不了,也模仿不了,是乡下的气候风物,民俗伦理,长时间在一个人身心上浸染,并且固化后的“土气”。憨并不全然是呆,也不全然是傻,它是一个包容的中性词,甚至是好词,如大巧若拙。有时候,一个憨人的细心和机灵,更让人咋舌。从湘西小镇走出的沈从文也带着憨。但两个人身上的憨又不尽相同,要是把沈从文比作是银杏树下的杏子雨,凉津津,带着深秋雨后的泥土气。那莫言则是弥天卷来的灰蒙蒙大雾里黑黢黢的高粱地。
莫言在《我的高密》中写过不少小时候的憨事,比如说他为了吃“浪费了太多的智慧”,偷吃,吃青苔,吃树皮。比如说他最早的记忆是掉进茅坑差点淹死,被大哥捞上后扛到河边洗澡。书里有一篇叫《草木虫鱼》,开篇写道:“我六七岁,与村中的孩子们一起,四处悠荡着觅食,活似一群小精灵。我们像传说中的神农一样,几乎尝遍了田野里的百草百虫,为丰富人类的食谱作出了贡献。那时候的孩子都挺着一个大肚子,小腿细如柴棒,脑袋大得出奇。我当然也不例外。”这些文字真是“憨”得活灵活现,漫画一般蹦跶出来。
莫言笔下的高密乡人,大多都有这样一种憨,有的命硬,有的命途多舛。憨人本就是一笔糊涂账,性子急躁,但坚韧不拔,做事投入,耐心周密,譬如《红高粱家族》里的余占鳌。《天堂蒜薹之歌》里形形色色的人物,高羊、高马、四婶、四叔、金菊,哪一个不痴,不憨?要是没有这诸多的憨人,恐怕也难以有莫言笔下高密乡这千秋大梦。
他当然也写过处境优渥的聪明人,《丰乳肥臀》中有出现过一个叫“马童”的孩子,爷爷是举人,家里良田万顷,骡马成群,上官鲁氏预言道:“像马童这样漂亮机灵的孩子,多半没有长寿,上帝给他的太多了,他已经占尽了做人的便宜,不可能再有一个寿比南山、子孙满堂的结局。”果不出上官鲁氏所料,不久马童就被枪毙了,是一个莫须有的“盗卖子弹”的罪名。
“虚则倾,中则正,满则覆”,有不偏不倚的憨劲,退让出一部分做人的便宜,反倒是能自全的中行之道。但聪明易学,憨人则是天生的。这属于天分的部分,最难得。
我喜欢莫言早期的作品,也是源于那种天生的尚未脱落的憨劲,《酒国》和《生死疲劳》虽然也喜欢,但整体很风格化和形式化,文字上的把戏和机巧越来越多,像是一个庞大的文学迷宫游戏,越写越聪明,却少了节制。反而《丰乳肥臀》,没有多线叙事,更一气呵成,气象已同于《百年孤独》。
三
我常会想,是怎么样的土壤才能孕育出一个说故事的天才。这种土壤,该是随意撒下一粒种子,次日便能千朵万朵花开;是随意劈开了一块石头,能蹦出个一筋斗十万八千里的孙猴子;是耒耜犁过,黑土地就能滋滋冒油,再翻开土地,黄麻就能呼吸歌唱;是广阔到看不见地平线的高粱海里,高粱们在齐头并进横冲直撞地咔嚓咔嚓长个。
莫言在《会唱歌的墙》写着草木,墨水河,池塘,堤坝,可触与不可触的颜色,几十万只酒瓶子砌成的声音的墙,如同一个母亲的絮叨:“世间的书大多是写在纸上的,也有刻在竹简上的,但有一部关于高密东北乡的大书是渗透在石头里的,是写在桥上的。”

电影《红高粱》
我高二时候看了电影《红高粱》,但一直没看莫言的原著《红高粱家族》,直到某天翻开了这本书,才惊叹过瘾。相较于电影,小说狂飙突进,时间线更长,也更加赤裸地不避讳地呈现着暴力。仿佛满桶满桶的颜料全喷在了纸面上,色彩斑澜、酒气、血腥气、高粱的甜味,一股脑儿全冒出来了,让人晕乎乎,醉熏熏,不知所踪。
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。莫言的高密,就如马尔克斯的马孔多,福克纳的约克那帕塔法县。《红高粱家族》开篇就气象不凡:
“高密东北乡无疑是地球上最美丽最丑陋、最超脱最世俗、最圣洁最龌龊、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、最能喝酒最能爱的地方。”
高密东北乡,确有其地。但要是真正探访,恐怕多数人要大失所望,不过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北方村子,并没有莫言笔下那般绚烂。但殊不知,作家杜撰是无罪的,反倒越能扯谎越富于想象力,越会被谅解和喜欢。莫言自己也说过:
“高密东北乡是一个文学的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的概念,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像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。”
这大概就是一个写作者的幸福了,他在里面大权在握,颐指气使,移山填海,呼风唤雨,他是造物的上帝,是执掌生杀大权的神明。

电影《红高粱》
四
小时候我爷爷经常给我说书。尽是些古怪的神鬼故事,比如说,铁拐李把腿放在灶里烧得吱吱作响,有人喊他说:“老头,你把腿烧瘸了。”他却全然不知,悠然自得。那人一头纳闷回家,发现自家的八仙桌缺了只腿,这才恍然大悟那老头是神仙。
长大之后,我在袁珂的《中国神话传说》,在《搜神记》,在《山海经》,在各种零落的旧书刊里,找到了我爷爷在灶台边给我说的很多故事,灶镬里的水滋滋扑腾着的那些时刻成了而今我最想念的时光。
我钟情于莫言,也源于此。莫言回忆童年时《封神演义》等志怪小说对整天沉浸在幻想中的他,具有难以抵御的吸引力。莫言出过一本小说叫《学习蒲松龄》,里面也尽是神怪之事。蒲松龄也是山东人,莫言说自己村里的许多人,包括他自己,都是蒲松龄的传人。而他的写作也可以追溯到这位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的异史氏。
神鬼并不让小时候的他感到恐惧,他恐惧的是人:
“世界上确实有被虎狼伤害的人,也确实有关于鬼怪伤人的传说,但造成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的是人,使成千上万人受到虐待的也是人。而对这些残酷行为给予褒奖的是病态的社会。”
所以,莫言的写作,除了对鬼怪妖狐的想象,另一部分无疑是在书写他的恐惧,关于人,关于社会。“写鬼写妖”,“刺贪刺虐”,这是郭沫若写蒲松龄的题联里的话。除了魔幻现实主义的西方语境,莫言也在蒲松龄这个传统小说的路子里,从早年的《酒国》到《蛙》,无一例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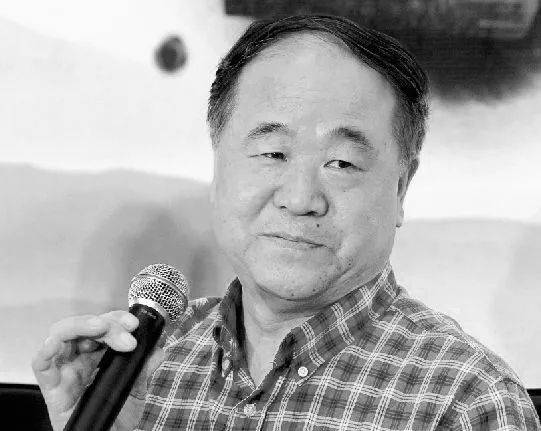
莫言
莫言去瑞典领奖,面对记者一些关涉到政治的提问时,会巧妙地回避开,譬如幽默地回答说:“我不要谈政治的事,我拿的又不是诺贝尔政治奖,如果拿政治奖我就谈政治,我们谈文学嘛,政治教人打架,文学教人恋爱。”
《锵锵三人行》有一期谈论到莫言在领奖时诸如此类的回答时,梁文道批评他过于“农民的狡猾”,是在避重就轻地周旋,“莫言现在拿到这样的身份地位,他是比我们所有其他体制内作家,更有资本,更有权利去做一个更加清晰的价值上的一个肯定或否定的判断”。
我不认同。这种是非的判断,是有代价的。莫言不是没有做过这种判断,他甚至比一般人批判得更深。要是他不关心政治,哪里还会有《天堂蒜薹之歌》这样的直笔之作,他在序言里写:“如果谁还幻想着用文学作品疗治社会弊病,大概会成为被嘲笑的对象。但就在这样的情况下,我还是写了这部为农民鸣不平的急就章。”
《天堂蒜薹之歌》以“蒜薹事件”为原型创作,它是我理解莫言的恐惧一部作品,理解了他说的“几十年来,真正对我造成伤害的还是人,真正让我感到恐惧的也是人”。这部悲剧色彩很重的小说,几乎每个人物都结局凄凉。小说各章节都以张扣的说书唱词为始,而这个说书人最终因为仗义执言,被警察用电棍塞到嘴中,嘣掉多个牙齿,死在了斜街,满嘴被塞满烂泥,此后“这斜街成了一条鬼街,民众纷纷搬走”。
张扣的境遇是隐喻,它预示着语言从来都是危险的。显然梁文道的批评太过苛责,世道再难,总得允许有人不哭的权利,他们或许只想呼吸顺畅,这也无可厚非。
我们姑且可以放松下紧绷的神经,给道德松松绑,就当莫言是一个篝火旁的说故事人,当他不想谈政治的时候,我们允许他不谈。毕竟文学是高于政治的。这样一个身份也许会让他和我们都轻松许多。人性中的恐惧与爱,是共通的,人性的脆弱总有一刻渴望被人谅解。
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:一点儿乌干菜(ID:NarratorZhang)。作者:章程,野生建筑师,青年写作者。豆瓣号:夜第七章